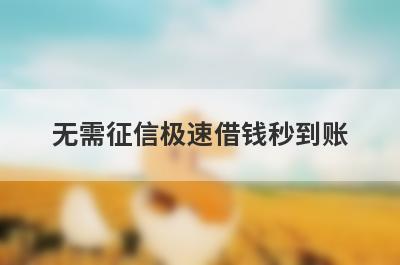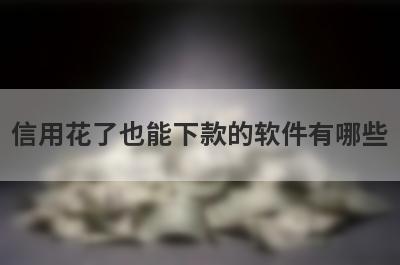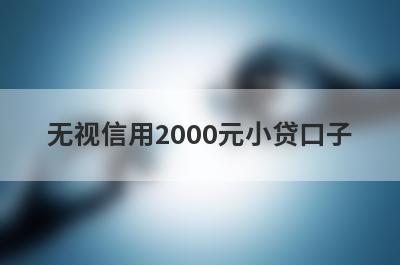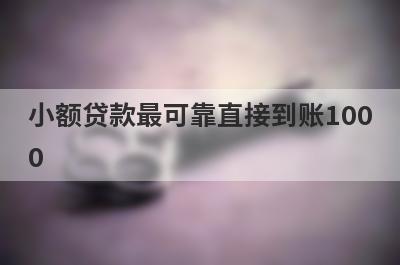烀苞米的味道(散文)
玉米在东北俗称苞米。在这片热土上广为流传着烀苞米的习俗。一进二伏,大田里的玉米刚要“定浆”,几乎农户每家都要烀上几顿苞米,俗称“啃青”,预示着当年好收成。
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烀苞米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乡村,都市的酒店经常会见到有烀苞米这道食材。早市上和大街小巷时常会听到烀苞米的叫卖声。也有农户把刚刚劈下来的苞米运到早市,堆成小山似的,卖给城里的居民。人们把吃烀苞米作为吃个鲜和调剂主食结构乃至养生的一种良方。
其实,城里的人很少有自己动手烀苞米的,得意这口儿的,买上几穗尝尝而已,谁愿意费事呢!
我的老家在辽西北的一个小村庄。故乡毕竟是乡愁,而烀苞米的味道,随着离开家乡岁月的流逝变成了遥远的回忆。
记得我小的时候,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,朴实的乡亲们认为苞米只有烀着吃才香,那是辛辛苦苦劳累一年的人们的口福。而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烙上了烀苞米是不可多得的一道美食。
在我的印象中,母亲烀的苞米在全屯子中是佼佼者。当我放学迈进院子的那一刻,烀苞米的香味诱我垂涎。母亲通常要给我挑个大穗的藏起来,然后像变戏法似的亮出来,犒劳我。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并老大,学习蛮好。我狼吞虎咽的啃着喷香的烀苞米,香在嘴里、心里。
半个多世纪,弹指一挥间。我思念我的故乡,因为它伴随了我的童年时光。更怀念烀苞米的味道,因为它一直萦绕在岁月的流年中。
幸运的是,十年前,我在城郊的荒野坨子上筑房定居,拥有了一处享乐暮年的田园。年复一年,春种秋收,烀苞米的习俗生生不息,浓浓的清香味道滋润着我的晚年生活。
田园虽小,种上几垄玉米,早种早收,目的是尽早吃上烀苞米,烀苞米的味道溢润着年年岁岁。记得烀苞米那天,我和老伴儿从一大早儿就开始忙乎。我找来几块红砖,搭起了临时灶台,把一米直径的军用大号铝锅往上一坐。
烀苞米看似简单,其实讲究不少,蛮有技术含量的。多年的经历我从舌尖上领悟到,用木头火比用煤火、柴禾火烀出的苞米味道更佳。我把备好的松木拌子,垛好堆在了灶旁。
玉米是高产的优良品种,一株结一到两个棒子,棒大粒饱,净粒足有一斤多。劈苞米时,先从几层叶皮扒开一条缝,用指甲掐一下老嫩,哧出白浆的最适合烀,稍嫩不老的吃着更是甜香。
接着,我和老伴儿一层层剥掉玉米叶子,只留下两三片,这样保证烀时不跑味。老伴儿干活麻利,抱起扒好的玉米棒子,一圈圈一层层的往锅里码,形状特像大盘向日葵,很是好看。码平口后,适量放些面碱和盐,使烀出的苞米口感柔软,香甜可口。挑一些嫩点的玉米叶,在浮头上铺上两到三层。再把洗好的茄子、土豆铺在最上层,添上与玉米持平的水,这叫“一锅出”。流程完毕,点火开烀。不大功夫,灶火兴旺通红,“叭叭”山响像放鞭炮,给整个院子带来了喜庆。
烀苞米的最大好处是省时省力,属于粗茶淡饭的那种,不必七个碟八个碗,备上农家菜就足够了。在院子中间,我把三个条桌并到一起,煮好的花生毛豆,蒸好的辣椒焖子,炸好的肉酱,切好的猪“下货”拼盘,咸鸭蛋,蒜末葱末香菜末,统统摆上了桌。盛了一大碗家酱,尖椒、小萝卜菜、倒池葱叶、苦麻菜、启麻菜、苏子叶、干豆腐片......,蘸酱菜应有尽有,看着都让人食欲大开。
我们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,男女老幼团团圆圆围坐在餐桌前,期待着别具风味的“盛宴”。当老伴儿把刚出锅烀好的苞米端上来时,那热气腾腾散发着浓浓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。小孙女高兴地又蹦又跳,可太热上不去手。老伴儿用一支筷子,用力插入棒的底部,让她拿着筷子啃苞米。孙女正处“脱牙”,在棒子上留下了一圈圈豁牙漏齿的“垄沟”,腮帮子上沾满了玉米白浆和玉米渣子,可香着呢。逗得大伙前仰后合。
岁月轮回,每逢这个时节,我们家都要烀上几顿苞米,多为自家人欢聚一堂,品尝着烀苞米味道所带来的甜蜜生活。也有时邀上亲朋好友、同学同事相聚,推杯换盏,如痴如醉,体验着原生态那种浓香触灵的乡息,回味无穷。
也不知道为什么,平时吃的山珍海味怎么也吃不出烀苞米的那种感觉和香味,是因为烀苞米的味道早已融入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,永远挥之不去。它不会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消失,反而因为岁月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清晰。
审阅:赵通
简评:这篇以烀苞米为主题的文章,汇聚了作者对昔日乡土生活的感怀及与亲人共处的浓浓情意。自然而亲和,淳朴而着实。
作者:李占忠
编辑:赵一
投稿邮箱:zxm789654@126.com(原创首发)
版权声明:本文为中乡美原创作品,未经允许,不得转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