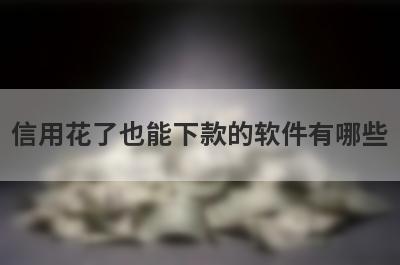我的童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,但是对于姥姥家的地锅我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印象。似乎只记得老姥姥、姥姥和小姨烧地锅的情形,只记得爱我的,我也爱的她们不时从锅底下用火棍拨出来的,一边拍打,一边吹着上面热灰的烤熟的红薯啦、枣啦、玉米棒啦、土豆啦等等。

这一切的一切的美好何时结束的?我也记不得了,大约是从上初中起就依稀离我远去了。我回到了这个陌生的,仿佛不属于我自己的家。家中吃饭的人口多,地又多,爸爸工作忙,我们都得做帮手。起初的我是不会做饭,我们家的饭菜有时是妈妈做,有时是大妹做,我烧锅。
似乎还记得第一次烧锅时,我把满屋弄的都是烟,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拉着风箱,还是没烧着。爸爸见状,走过去,从地上抓起一把软柴火,好像是麦秸,点火引着,接着一点儿一点儿的向里面放硬柴火,大概是树枝,约略又放了一把麦秸,又过了会儿,把火烧旺后才交给了我。好大一会儿厨房里的烟才散尽。约莫过了几分钟火又一个劲的向外冒,厨房里又逐渐有了烟(家里地锅有烟囱,按理说不该有烟)!唉,我可能根本不是烧锅的料!这比解个方程难多了!
爸爸又走了过来,可能在外面看到了浓烟。他蹲下身子,把后面的带着火星的热灰、还有一些没燃烧透的树枝扒到炉篦上,热灰顺着炉篦落到了地锅最下面的炉洞里,然后把门口燃烧着的树枝向里送到炉篦处,最后又用火棍把树枝摊开,向上挑了挑,一边挑,一边说,“心要实,火要虚。”
你还别说,这还真把当时的我惊诧了一番,烧锅这么小的事中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学问!后来烧锅的活是基本上都是我的了,即使后来我学会了做饭,我也不想做,似乎做饭更麻烦,小懒的我每次和妹妹一起合作做饭,总是飞快跑到锅门前的凳子上,瞬间坐下,站取有利地势(现在想想,给比我小的妹妹抢轻活干实在不应该,可是当时在姥姥受百般宠爱的我哪知道什么是谦让。)。
后来的后来我就上学离开了家,再后来我又上了班,再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每次回家地锅都是由不再工作,稍有闲空的爸爸去烧,即使有时我坐到锅门口,爸爸也会把我拉开。今天恰好爸爸去镇上赶集去了,我又当了回伙夫。看着锅底熊熊燃烧的玉米轴心,我又想起了坐在锅门口,拿着火棍轻一下,重一下拨柴,拨灰的那个小小的我,又记起了那个踮起脚尖做饭的比我还小妹妹,又回味起了姥姥家烤红薯、烤红枣、烤玉米、烤土豆的香味……